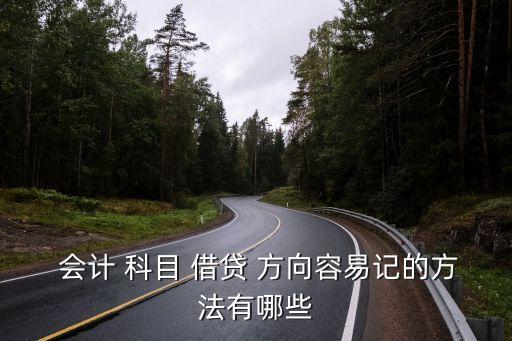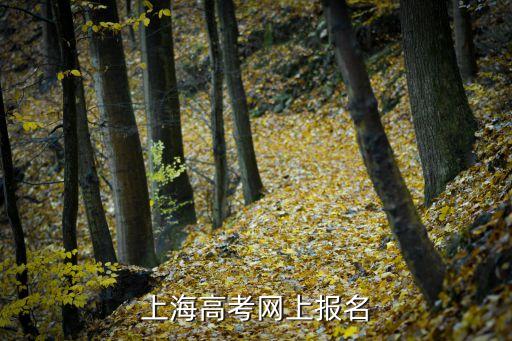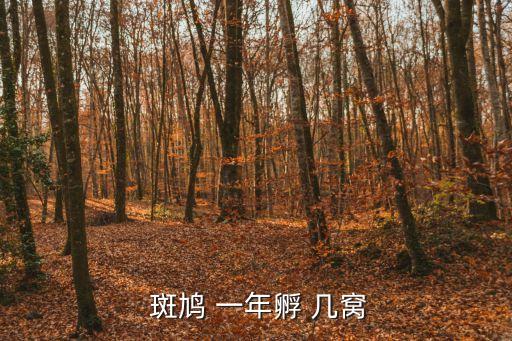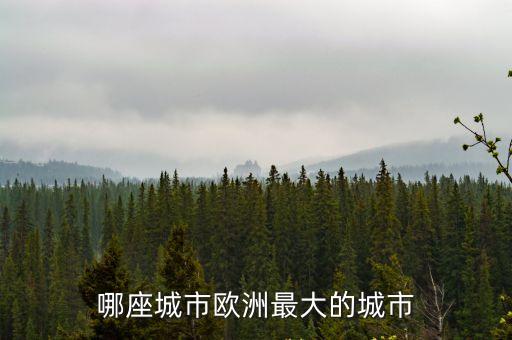(洛陽)洛陽與長安相距并不遠,在長安大旱時,實際上洛陽也有旱情。(長安)實際上,從唐高宗時期開始,洛陽就被確定為唐朝的東都,到了武則天時,更是將辦公地點搬到了洛陽,將洛陽命名為“神都”,雖然洛陽和長安都經歷過戰火和災害,但是洛陽的災情比較單一,受災程度也遠遠小于長安,更為重要的是,洛陽擁有優越的糧食供應保障。
1、為什么定都洛陽興盛,定都長安衰亡?

都長安者盛世統,遷洛陽者天下分。我們看看先賢顧祖禹在《讀史方輿記要》中怎么說:“陜西居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陜西之在天下也,猶人之頭項也”!這就是“關中者天下之脊,中原之龍首也”的形象寫照。“河南古所稱四戰之地,當取天下之日,河南所在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周之東也,以河南而衰;漢之東也,以河南而北;拓跋魏之南也,以河南而喪亂,
2、唐朝時期為何要定都長安,后來又定都洛陽?為何?

長安是唐朝的首都,也是唐朝中前期的政治和經濟中心。長安歷史悠久,地處八百里秦川之中,交通便利,物產豐富,擁有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地位,但是唐朝中期之后,隨著長安地區人口不斷增加,這個百萬人口的大都市對唐朝來說,是一種榮耀,也是一個大包袱。因為長安及附近地區人口爆漲,給唐朝政府形成了極大的人口壓力,而這一時期,長安附近地區水旱頻仍,糧食供應也一度非常緊張。
因此,唐朝統治者不得不選擇一個物產更為豐富、交通更為便利的地區,去分擔長安的人口壓力,緩解關中地區緊張的糧食供應,而與長安相距并不十分遠的另一個古都洛陽,便是唐朝最好的選擇。(長安)實際上,從唐高宗時期開始,洛陽就被確定為唐朝的東都,到了武則天時,更是將辦公地點搬到了洛陽,將洛陽命名為“神都”,洛陽也因此成為唐代長安之外一個政治、經濟中心,在唐朝的歷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所以說,爆漲的人口和環境的惡化造成了唐朝政治經濟中心的東移,而這種環境上的惡化,是由長安持續不斷的水、旱災害引起的,一、唐朝的氣候特點氣象學專家對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的三百年間長安和洛陽兩地的自然災害進行過統計,在這三百年中,長安地區發生水旱災害共有119次,而洛陽地區僅有58次,長安是洛陽的兩倍還有余。
雙方在水災發生次數有一定的同步性,相差不是特別大;但是旱災方面,長安遠遠多于洛陽,而且災情比較嚴重,頻率也很高,我們觀察一下氣象學上著名的“竺可楨曲線”,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自公元六世紀開始,中國經歷了一個歷時四百年的“暖期”,也就是“隋唐溫暖期”。根據對一些古樹年輪的研究,這個暖期的前期是一種暖濕性的氣候,當時中原地區的整體溫度比今天要高0.3到0.5攝氏度,
而公元780年到920年間,又出現了一個“冷谷”,平均氣溫又比現在要低0.8度左右,甚至在部分地區氣溫低于“明清小冰期”。(洛陽)這種氣候上的變化,導致了唐代中前期氣候暖濕,后期冷濕,但總體降水較多,受這種氣候影響,長安、洛陽所在的黃河流域和關中平原,都表現出水災中間多,兩頭少;旱災中間少,兩頭多的特征。
表現在水災和旱災上,兩地在唐朝前期和后期以旱災為主,而中前期和中期以水災最為常見,二、旱災對長安和洛陽的影響據《舊唐書》記載,唐中宗之前,長安附近出現過大的旱災共有四次,其發生年份為貞觀十三年、二十三年;垂拱元年和久視元年。這幾次旱災受災面廣,持續時間長,對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唐朝經濟和農業生產帶來了極大的打擊,對長安地區的百萬居民吃飯產生了嚴重的威脅,
《舊唐書》對貞觀十三年的大旱是這樣記載的:“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甲寅,避正殿,令五品以上上封事,減膳罷役,分使賑恤,申理冤屈,乃雨”,(長安)這次旱災,使得長安地區無法播種,幸虧此時隋朝積攢的大批義倉之糧尚未腐壞,李世民緊急調運這些隋朝留給自己的糧食,才勉強解決了長安地區的吃飯問題,要不是當年楊廣的庫存,這次大旱對唐朝和長安居民造成極大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