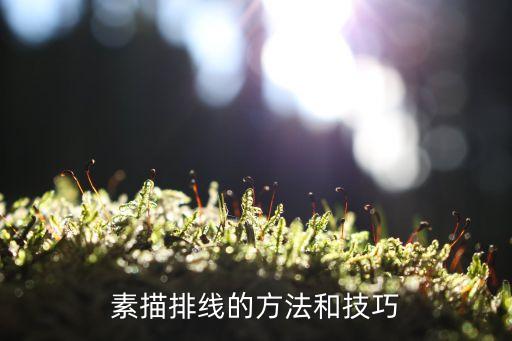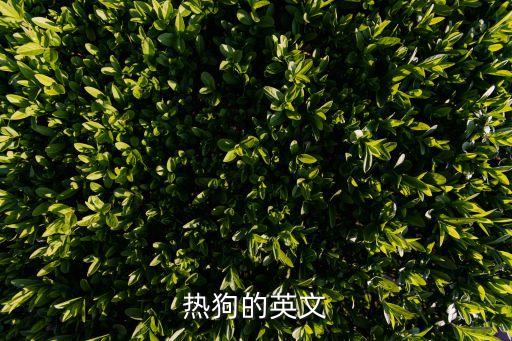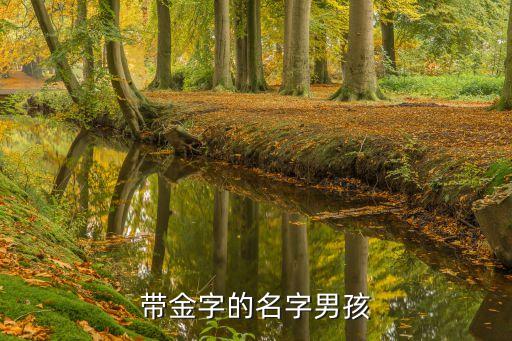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臥龍。南陽諸葛廬與“躬耕南陽”在表述時也不存在任何矛盾,不像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將隆中與“躬耕南陽”掛鉤時要扯出諸如“屬南陽鄧縣”、“不屬襄陽”、“郡望說”、“漢水如何如何”等等條件來圓這個說法,故隋唐文人在談及南陽諸葛亮時大都比較直白和簡潔。
1、“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中的南陽是指現在河南的南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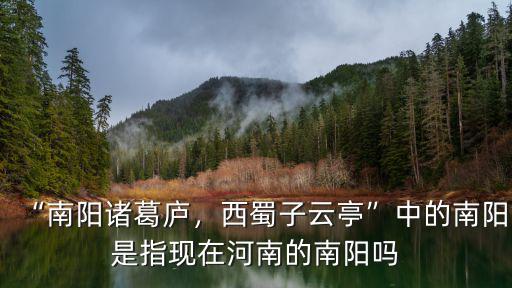
當然了,從建安十三年(劉備三顧茅廬之后的第二年)曹操設襄陽郡以后,不僅漢水南岸的隆中不屬于南陽郡,連漢水北岸的樊城也不屬于南陽郡了,唐代更不用說了。除了白癡,誰還會把襄陽稱為南陽?就像我們今天說去南陽開會,襄陽人還能膩膩歪歪說這個南陽是隆中嗎?在隋唐時期,由于結束了魏晉南北朝南北割據的局面,南方文人不再將諸葛亮作為“光復中原”的楷模,北方民眾和官員出于對諸葛亮的尊重和崇拜,也逐步加強了對“躬耕于南陽”和南陽諸葛廬的認知和回歸,
由于唐代南陽與襄陽已不存在漢水為界的問題,宛縣已改名為南陽縣,今隆中地區屬于襄陽縣也不存在任何異議。所以,南陽諸葛廬與“躬耕南陽”在表述時也不存在任何矛盾,不像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將隆中與“躬耕南陽”掛鉤時要扯出諸如“屬南陽鄧縣”、“不屬襄陽”、“郡望說”、“漢水如何如何”等等條件來圓這個說法,故隋唐文人在談及南陽諸葛亮時大都比較直白和簡潔,
加上這一時期諸葛亮“躬耕南陽”和諸葛亮開始由歷史人物向藝術形象的過渡,所以出現了大量記述南陽諸葛亮的詩文和碑記,一改南北朝時期只有隆中“亮家說”,沒有南陽“躬耕說”的局面。丁保齋在所編《隆中志》收錄的胡曾的《隆中山》兩首問題很大了,其一:“亂世英雄百戰余,孔明方此樂耕鋤。蜀主不自垂三顧,安得先生出草廬,
”其二:“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釣。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嘆白頭,”(見《隆中志》第101頁)按《隆中志》的觀點,這兩首詩名《隆中山》,肯定是在隆中所作,是在詠吟隆中的孔明遺跡。但第一首詩我們在前文已經引用過,是收入《臥龍崗志》的同為胡曾的詩,南陽所收該詩的名稱為《詠史詩?南陽》,這就針尖對麥芒了,同一首詩,同一個人,兩個名稱,兩個地點。
肯定是一個真,一個假,孰是孰非?其實,這個問題一點兒也不難解決,查查這首詩的來源《全唐詩》一切就都清楚了,《全唐詩》卷六百七十四第二十八首為《詠史詩?南陽》,第三十首為《詠史詩?渭濱》,正是《隆中志》所收入的兩首胡曾的詩,但名稱不是“隆中山”,而是“南陽”和“渭濱”。顯然,《隆中志》在胡曾詩的收錄上,采用了“移花接木”、“指鹿為馬”的錯誤手法,誤導了讀者,
2、河南南陽是一個怎樣的城市?

我是東北人,按理說沒什么權力去評論南陽的,可是我的網上的朋友還真有很多南陽人,我有個微信群的群主就是南陽人,因此無疑讓我對南陽就有了更多的的好感的!還真去過南陽,所以對南陽的印象還是挺深刻的,前些年,曾幾次去過去鄭州,有一次負責接待的朋友恰巧老家就是南陽人,在安排完去了少林寺參觀完之后,他說要帶我們幾個不錯的朋友去他們家看看,他就弄了臺中型面包車,拉了我們七八個人去了南陽,而他的老家則是在豫西的大山中,所以那一次就去了南陽,進了豫西的大山之中!那一次的南陽之行也就讓我記住了南陽,南陽的美好的印象就留在了我的心中!所以看見這個問題也就簡單的說了幾句,以表示我對南陽的的懷念,及對我那個南陽朋友的懷念之情吧!最后祝南陽的新老朋友們開心快樂,幸福安康,祝南陽更富裕更美好!【社會現象,家庭問題,獨家觀點,解惑釋疑。
3、“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臥龍”,含有哪三個人?

感謝邀請回答,“文章西漢兩司馬”是晚清重臣左宗棠為臥龍崗諸葛草堂所題寫,原詩: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臥龍。心同佛定香煙直,目極天高海月深,出處動關天下計;草堂我也過來人,此詩前兩句之意:文章寫的好是西漢司馬遷和司馬相如,而濟世經邦的人才則要首推諸葛亮了,就是指司馬遷、司馬相如和諸葛亮三人。司馬遷(公元前145-前87年前后),字子長,西漢夏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