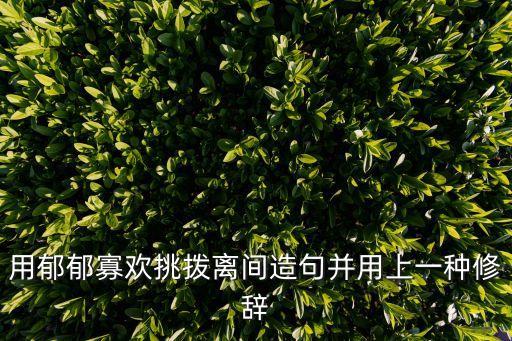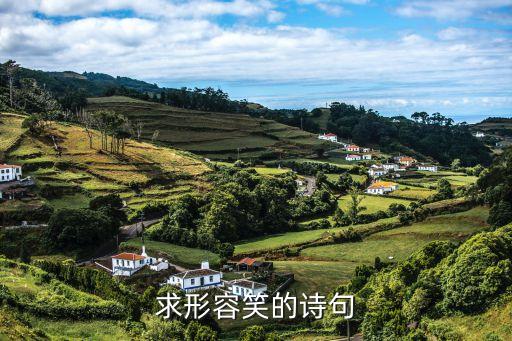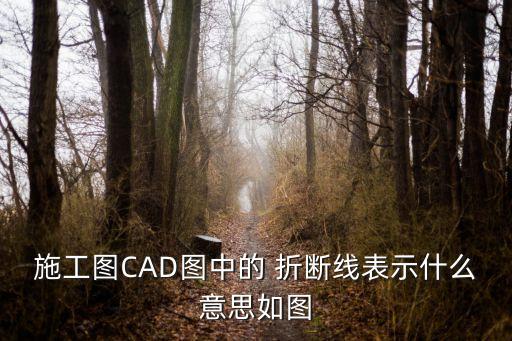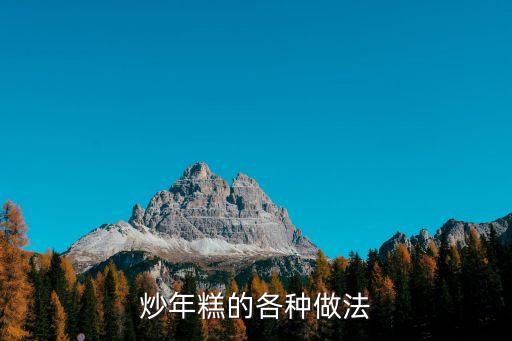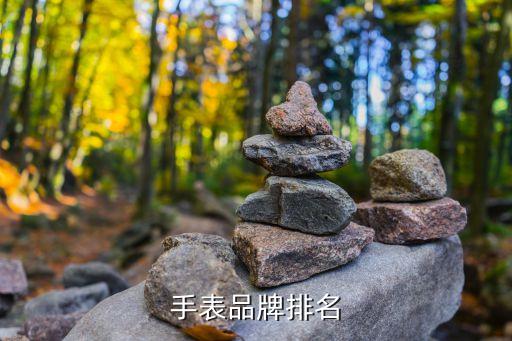加上這一時期諸葛亮“躬耕南陽”和諸葛亮開始由歷史人物向藝術(shù)形象的過渡,所以出現(xiàn)了大量記述南陽諸葛亮的詩文和碑記,一改南北朝時期只有隆中“亮家說”,沒有南陽“躬耕說”的局面。諸葛亮說的躬耕于南陽是指當(dāng)時的南陽郡,而非宛城(今南陽市),光知道弄一些無稽之談否定南陽郡郡名與郡治互指,否定諸葛亮親口說的“躬耕于南陽”的南陽不是當(dāng)時的南陽城。
1、為什么有人認(rèn)為諸葛亮的后人每年拜祖是到湖北的襄陽,而不是河南的南陽呢?有何依據(jù)?

河南方主要依據(jù)諸葛亮寫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認(rèn)定南陽可笑至極,無知至極(早詳細(xì)論述過,可查詢到的)。國家于1996.5.28早定論(網(wǎng)上有)并由中央廣播臺公布(我親耳聽到的,自此關(guān)注此事)躬耕地在今襄陽隆中了(古南陽郡鄧縣隆中,襄陽城西20里處),南陽失利方黔驢技窮近20余年都不服、胡鬧——胡說什么古、今造假(改史)之類、賄賂之類,這樣說的可信依據(jù)呢?這些倒很讓人唏噓、鄙視!河南人尤其是南陽人服不服以上定論也得服的。
諸葛亮后代(浙江、廣西據(jù)說都有分布)最近于2018年9月9日去(此前也多次去過)襄陽隆中紀(jì)拜祖先,但絕不去南陽臥龍崗偽躬耕地也是有力的證明,諸葛的后代人(主要在以上2省部分地方)比河南人尤其是南陽人傻嗎?我可不是豫、鄂人,也不是那方水軍、槍手,我只宣傳事實(shí)(包括詳細(xì)論述)達(dá)到平息爭論,。個人估計(jì)河南省外的人大都認(rèn)可這20多年前的定論的,要河南人也認(rèn)可還要幾十年的,
2、“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中的南陽是指現(xiàn)在河南的南陽嗎?

當(dāng)然了,從建安十三年(劉備三顧茅廬之后的第二年)曹操設(shè)襄陽郡以后,不僅漢水南岸的隆中不屬于南陽郡,連漢水北岸的樊城也不屬于南陽郡了,唐代更不用說了。除了白癡,誰還會把襄陽稱為南陽?就像我們今天說去南陽開會,襄陽人還能膩膩歪歪說這個南陽是隆中嗎?在隋唐時期,由于結(jié)束了魏晉南北朝南北割據(jù)的局面,南方文人不再將諸葛亮作為“光復(fù)中原”的楷模,北方民眾和官員出于對諸葛亮的尊重和崇拜,也逐步加強(qiáng)了對“躬耕于南陽”和南陽諸葛廬的認(rèn)知和回歸,
由于唐代南陽與襄陽已不存在漢水為界的問題,宛縣已改名為南陽縣,今隆中地區(qū)屬于襄陽縣也不存在任何異議。所以,南陽諸葛廬與“躬耕南陽”在表述時也不存在任何矛盾,不像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將隆中與“躬耕南陽”掛鉤時要扯出諸如“屬南陽鄧縣”、“不屬襄陽”、“郡望說”、“漢水如何如何”等等條件來圓這個說法,故隋唐文人在談及南陽諸葛亮?xí)r大都比較直白和簡潔,
加上這一時期諸葛亮“躬耕南陽”和諸葛亮開始由歷史人物向藝術(shù)形象的過渡,所以出現(xiàn)了大量記述南陽諸葛亮的詩文和碑記,一改南北朝時期只有隆中“亮家說”,沒有南陽“躬耕說”的局面。丁保齋在所編《隆中志》收錄的胡曾的《隆中山》兩首問題很大了,其一:“亂世英雄百戰(zhàn)余,孔明方此樂耕鋤。蜀主不自垂三顧,安得先生出草廬,
”其二:“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dú)垂釣。當(dāng)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嘆白頭,”(見《隆中志》第101頁)按《隆中志》的觀點(diǎn),這兩首詩名《隆中山》,肯定是在隆中所作,是在詠吟隆中的孔明遺跡。但第一首詩我們在前文已經(jīng)引用過,是收入《臥龍崗志》的同為胡曾的詩,南陽所收該詩的名稱為《詠史詩?南陽》,這就針尖對麥芒了,同一首詩,同一個人,兩個名稱,兩個地點(diǎn)。
肯定是一個真,一個假,孰是孰非?其實(shí),這個問題一點(diǎn)兒也不難解決,查查這首詩的來源《全唐詩》一切就都清楚了,《全唐詩》卷六百七十四第二十八首為《詠史詩?南陽》,第三十首為《詠史詩?渭濱》,正是《隆中志》所收入的兩首胡曾的詩,但名稱不是“隆中山”,而是“南陽”和“渭濱”。顯然,《隆中志》在胡曾詩的收錄上,采用了“移花接木”、“指鹿為馬”的錯誤手法,誤導(dǎo)了讀者,
3、三國諸葛亮隱居的南陽,和現(xiàn)在的河南南陽市是同一個地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