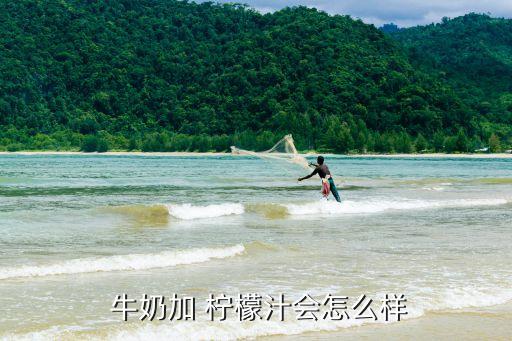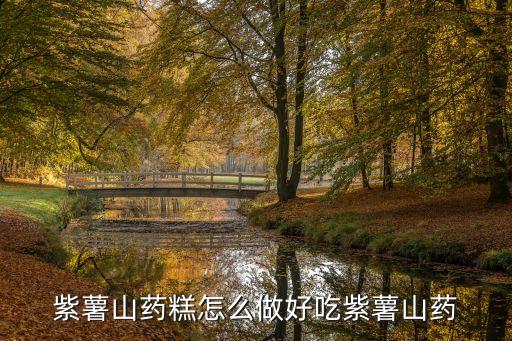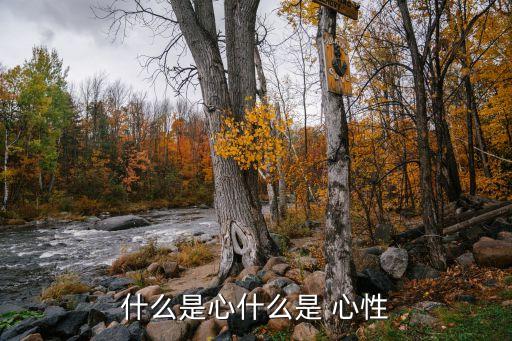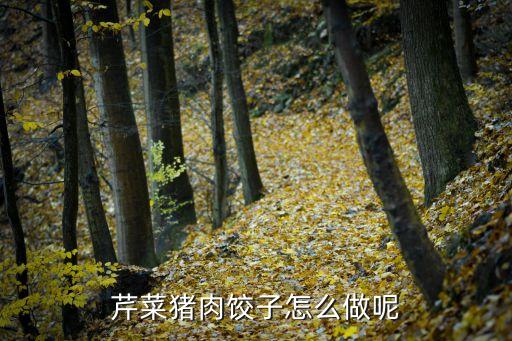在他看來,“惟精惟一”的態度和方法在各種學習、修養中具有普遍適用性,王陽明在回答弟子的提問時說。“好在哪里”是要具體分析的,這是王陽明心學在理學史上發展的“好”處,在王陽明看來,“理”不在外部事物,而在人的心中,是心中的道德良知,”(王陽明《重修山陰縣學記》)“十六字訣”中的允執厥中在這一段話中,王陽明有兩個解釋是很有創見的。
1、王陽明最打動人的地方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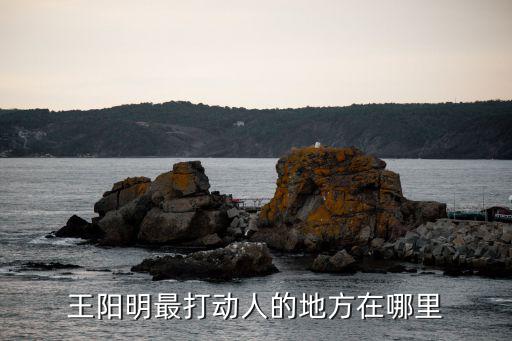
我認為王陽明最打動人的地方,就是在貶謫到貴州龍場期間。發揮其主觀精神,終于大悟了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龍場頓悟》。如果是一個普通人來說,受到這樣的打擊,處于這樣的逆境中,肯定會耿耿于懷,總想有朝一日伺機報服,然而王陽明忘掉自我,日夜端居澄默,以求盡一,胸中灑脫,“求理于吾心”。
就是從自身找原因,就憑王陽明這一思維,真是讓后世人感到王陽明的心胸是多么寬廣,多么品德高尚,真是打動人心,值得當今社會的人們學習。在貴州龍場三年,為當地老百姓掃除文盲,受到老百姓的愛戴,遂入心學之門,授徒講學,聲明遠播。后又受貴州府學者之聘,到府城設立書院講學,最終得到朝庭認可。期滿后又得到朝庭的重用,巡撫贛南,消除匪犯,平定寧王之亂等,逐步走向建功立業的輝煌士途,
2、陽明心學到底好在哪里?
要知道王陽明心學到底好在哪里,要從多方面去分析,從比較高的理論方面分析,是必須闡述王陽明心學在宋明理學發展中的理論貢獻和重要意義;從王陽明理論體系本身來看,是要闡明他對心學有什么理論貢獻和創新見解;而從實際王陽明心學學說給人們的哲學啟發來看,是要說明王陽明的心學,特別是他的“致良知”理論對于現代人有什么哲理方面和方法方面的用處,即心學的實際啟迪意義。
所以,“好在哪里”是要具體分析的,先說第一方面,王陽明的心學是全面繼承和發展了陸九淵的思想,所以,歷史上有“陸王心學”之說。當然,王陽明所繼承的陸九淵的思想只是主要的方面,而他所繼承和發揮的是整個兩宋理學家們的思想,特別是揚棄了二程(程頤、程顥)和朱熹的思想,據說,王陽明在十五、六歲的時候便開始閱讀朱熹的著作,開始鉆研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論,他曾在他的朋友的院子里對著竹子“格物”了七天,病倒了,但依然并沒有能悟到物的道理,弄不清“理”在哪兒。
知道他三十幾歲時,因上書要求制止宦官專權而被貶到貴州龍場任驛丞,王陽明在龍場日夜靜思,才悟出了心學的真正道理,這就叫“龍場悟道”。“龍場悟道”由此,王陽明認為按朱熹說的方法去“格物”,是行不通的,只有按他自己的悟,才能悟出道理,“格”竹子是錯的,“竹子”里沒有“理”,“理”其實就在自己心中,依此,王陽明提出了他的哲學的基本理念——“心即理”,
這就是王陽明心學的理論基點。所以,在王陽明看來,“理”不在外部事物,而在人的心中,是心中的道德良知,王陽明說:“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傳習錄》)他認為,理不是朱熹說的“天理”而是人心中的道德意識,王陽明據此而把他的理論傳播給他的學生,建立了新的心學,并提出了“知行合一”理論。
他認為,真正的“知”,是一定能夠“行”的;而真正的“行”,也一定是包含“知”的,王陽明說:“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傳習錄》)知與行其實都是一種功夫,他說:“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當然,二者既有區別,又是本質一致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知和行是不能隔離的,先知而后行是不對的。陽明講學在王陽明看來,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可分離;知識行的出發點,是用以指導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已在行中;行是知的歸宿,是知的實現,而真切篤實的行已自明察知在起作用;知行工夫統一的目的,就是去除“不善的念”,使心恢復善性,因而,知行統一就是“致良知”,而“吾心良知”即是“天理”,“知行合一”其實是“致良知”這一功夫的兩個環節。